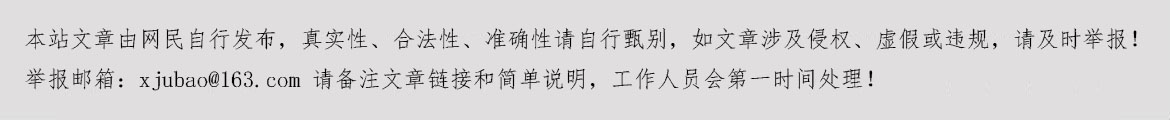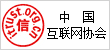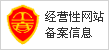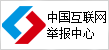一排光溜溜的肉体,站在监区的大院子里,甚至连私处都懒得遮掩下
2022-02-24 18:03:02
【本文节选自网文作者:北邙,有删减;图片来自网络;如有侵权,请联系删除】
一排光溜溜的肉体,站在监区的大院子里,他们脚边是散落一地的衣服,刚刮好的头皮青楞楞的,在夕阳的余晖下,反射出锃亮的光。
夏末的尾巴还没走远,空气有些燥热。这六七个脱光了的人说不上什么害羞,反而带着点光棍的痞气,抖着腿站在那,甚至连私处都懒得遮掩一下。他们的身上大多留着纹身,青色的墨水刺成歪歪扭扭的文字,一眼就能看出街边小店的廉价手艺。
我时常说,监狱工作这几年,见的世面比过去二十年都多得多。
其中,男性的裸体就是这些「世面」里占比极重的一环。
新犯入监第一道槛,排着队把看守所带过来的衣服全脱光,装包收纳入库,出狱的时候再领。然后光着身子过两道监控门,再被人肉搜一次身,确定没有带任何违禁物品在身上之后,换上统一的囚服被褥,送去监房安顿。
说实话,我对同性的身体没有半毛钱兴趣,乍看之下甚至有点意味不明的反胃,可工作所迫,见得久了,吐着吐着也就习惯了。然后等到再看的时候,竟然有点自己像是澡堂干了大半辈子的看门老大爷的感觉,对有些新入监的、还遮遮掩掩的犯人甚至有些不耐烦——「不就是那几两肉吗,有什么好藏着的,谁见得少了还是?都给麻溜点!」
但那天,就在我百无聊赖地坐在门口椅子上,跟过来办交接的看守所民警有一茬没一茬地聊着天,等着交接手续办完的时候,队伍后面忽然鼓噪了起来,像是有犯人交头接耳,夹杂着一声倒吸一口凉气的声音。
新犯光着身子排队检查的时候,负责搜身的有老犯——各监房的组长和一些特殊岗位的小岗——也有民警,但是一般老民警照顾我们年轻人,大部分情况我们只要在边上看着,真正去搜身去摸的都是经验丰富、年纪也大了不太避讳的老民警们。
那天跟我搭班的老民警姓田,还有两年退休,是从别的监区长位置退下来后,来我们这儿「养老」的,以他快四十年的监狱工作经验,我很难想象是看到了什么,能让他这么吃惊。
很快,还没等我站起身来张望,队伍后头的鼓噪声就大了起来。
「怎么回事?」我连忙问。
负责搜身的老犯从队伍后面走过来,皱着眉头,右手在鼻子前头连连扇风:「郑队,你别看,太恶心了。」
「啥恶心?」我不屑一顾,再恶心,能有孙超的床铺恶心?
「最后头那个犯人,老头,少数民族的,叫什么火布……什么甲来着,妈的,太瘆人了,不能看第二眼。」
他越是这么说,我反而越好奇了起来,从大门口往队伍后头走去,没两步,就看到老田身边站着一个犯人,低着头,一声不吭。
那是一个老头,看起来五六十岁,脸色黝黑,五官有些怪异,第一眼看上去,就会让人想到缅甸、金三角和云南,他佝偻着背,身材很瘦,肋骨一根根地凸出来,被干枯的皮肉勉强包裹着。他的双手自然垂下,老田正用两根手指拈起他的手腕,盯着他的胳膊,深深皱着眉头。
我走近了两步,才看清他胳膊上的东西,忍不住打了个寒颤,大腿上顿时起满了鸡皮疙瘩。
他的两只胳膊上,竟然密布着一个个大大小小的肉洞。
那些洞大的约莫西瓜子般大小,小的只有芝麻粒一样,没有脓血,只是黑漆漆的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年老和太瘦的缘故,他一双手的皮肉都向下耷拉着,那些洞好像天然就长在他的胳膊上一样,远看像是点点深褐色的红斑,带着些溃烂,有些洞的外头翻卷开来,甚至能看到血管和纠缠的肉瘤。
再仔细看,才发现他的两只手都没有手指——只有右手还剩着两截像是被剁掉一半的手指疙瘩,皮肉都完整地长在了一起,不知道已经这样多久了。
「什么病?传不传染?」我倒退了两步,捂着鼻子问。
老田经验丰富,努了努嘴,示意我看他的脚。
他的双脚竟然也没剩下几根脚趾,畸形得像是古代女子缠足后的小脚。指甲粗粝黝黑,翻在一边。他的大腿上也有不少和胳膊类似的肉洞,令人不敢多看半眼。
「吸毒多久了?」老田拖着嗓子问,语气里遮掩不住的厌恶。
老犯一声不吭,像是没听到一样。
看守所的民警此时也走了过来,摆了摆手:「田大,别问了,是个彝族人,老毒贩了,不会说汉话,脑袋也糊涂了。」
「贩毒的能不会说话?糊涂,我看是装糊涂。」老田哼了一声,把这个老犯的手腕甩开,掸了掸手,「叫什么名字?」
「火布古甲,48岁,贵州人。六进宫了,十几岁开始吸毒,吸了三十年还没死,也吸毒,也贩毒,也容留吸毒,看到他的手指跟脚趾没有,都是被毒贩子给剁的。」看守所民警看来也对这个老头很了解,没有翻档案,说起他的资料来如数家珍。
「贩毒怎么还要剁手指?」我站在一边,好奇地问。
「跟人拿了货之后,没卖出去多少,自己毒瘾犯了给吸了。本钱都捞不回来,那钱都是跟毒贩子贷款借的,白粉也没了,钱也没了,按照他们的规矩。要剁手指,让他长记性。结果这老头也厉害,三十年,手指剁完剁脚趾,二十根指头都快剁干净了,还是照样吸毒,那些给他借钱的毒贩要么枪毙了,要么吸毒吸死了。他牛逼,活得好好的,跟没事人一样。」看守所民警啧啧称奇。
我也跟在一边砸吧嘴:「都这样了,还有人愿意借款给他?」
「怎么没有?他在他们那道上也是出了名的老混子了,干的那点破事谁不知道,有不少人借个万八千的给他,让他拿毒品去卖,根本就没指望他能还钱。就是冲着剁他根手指玩,刺激,出去之后吹牛逼,手里也是见过血的。」看守所民警摇了摇头,「烂命一条,以后你就知道了。」
火布古甲进来之后,我一直留了个心眼,对他特别关注。
他被分配到了411监房,监区里著名的「神仙窝」。用我们文教的话来说:「411?那谁敢管啊,里头住着一窝子神仙!」
这话是真的。关着八个老头的409有人管,关着孙超的401有人管,唯独这411,没人愿意管,开了几次会,最后没办法,林大带着文教,监区的一、二把手亲自挂牌,负责下了这个监房。
火布古甲是这个监房的第六个犯人。
前头那五个,一个比一个难缠。
第一个是被两名武警用枪押着、穿着束缚衣被绑的严严实实的送进监狱的,在监区的地位约等于魔法世界里的伏地魔,开会提到他连名字都不带,直接称呼「411的那鬼东西」。他是重度狂躁症加精神分裂,发起疯来跟不要命一样,创下了监区至今唯一一个徒手掰弯了铁栏杆的纪录——当然不是真的用手,而是用脑袋撞弯的。平时关在监区最深处,犯病的时候咆哮嘶吼,咚咚咚撞墙,知道的以为是精神病发,不知道的恐怕还以为我们监区里头封印了一头什么狂化的半兽人呢;
第二个是个四十多岁的生意人,也是个监区记录的保持者,保持了所有犯人里自杀次数最多的记录。他也不是真自杀,而是总能想出花样百出的法子,吆喝着假装要自杀。比如用裤子拴在上铺的床沿上,套在脖子上然后从上铺爬下来,声称是上吊。再比如用锋利的纸划破自己的手腕,虽然只是破了一点点的毛细血管,但是也号称着割腕了。他基本上过个个把星期就要自杀一次,以求去医院里躺着,提出一些乱七八糟的无理要求;
第三个是一个人格障碍患者,通过了精神鉴定测试,确诊病症,而且有明显的第二人格迹象。和其他精神病患不同的是,他是因车祸造成的器质性损伤,别人的脑袋是一个圆形,他的脑袋不一样,从颅顶一点到右耳部位,这小半个脑袋被切掉了,上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头皮,连带着右脸的眼睛鼻子都是歪的。听说车祸之前本来是正常的,自从脑袋少了半个之后,就彻底疯了。
第四个则是个小混混,重度被迫害妄想症。每天半夜不睡觉,疯狂按铃,要么声称有尸体在走廊上走,要么说有小孩在天花板上看着他。每次汇报思想,都说自己被老婆派来的很多小人监视着,那些小人想找机会杀了他,弄死他,逼疯他。可他就是不死,他要好好活着,出去之后杀了老婆。
最后一个最厉害,叫刘瞎子,是个北方农村里的老神棍,据他自己吹牛,在当地是赫赫有名的半仙,多少人驱车不远千里,就为了来找他算一卦。收成最好的时候,有一年大年初一,从早上5点算到晚上10点,一天赚了八十多万。他的左眼是全瞎,右眼还有0.2左右的视力,但他总是自称瞎子,一副什么都看不到的样子。他进来的原因也有意思,找了几个最虔诚的信徒,借了一千两百多万,可借完不还了,被人告了进来坐牢。他自己还振振有词:「我那手机里都有录音,是他们拜我为师,上供给我的,都是主动供奉的,不是借!千儿来万算个什么事?还把我给告进来,瞎胡闹。」
火布古甲进来后,成了神仙窝里的第六个神仙。
不会说汉话,没有手指,没有脚趾,一个活了三十年的老毒贩,传奇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前头五个——我后来才知道,他的胳膊和大腿上满满的都是吸毒留下来的针孔,皮肉松弛之后再也愈合不上,才形成了这大大小小的肉洞。
起初的时候,我担心过他的毒瘾发作了怎么办。
我们监狱里没有专门的戒毒队,与毒品有关的犯人很少,大部分是专门管理,火布古甲还是我接触到第一个有可能在监狱里毒瘾发作的犯人。我为了这个,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特地请教了文教,文教却摆了摆手,说他当时在火布古甲过来的时候,就跟当地公安和看守所的人对接过了,说这个老头没事,不会发作的。
「吸了三十年的毒,没毒瘾?」
「唉呀,不是没瘾,是他毒瘾发作太多次了,已经麻木了,他十几年前就没钱吸毒了,一直断断续续的,有了就抽点,没了就熬着,多少次差点就直接死过去了,结果没死透,捡了条烂命回来。他之前在看守所待了大半年,也都没事,顶多是抽抽一阵子,自己就好了。」文教点了根烟,说的头头是道。
「还有这种事,毒瘾犯多了,自己能有抵抗力?」我第一次听说这种说法,有些半信半疑。
「你问我,我问谁去。我跟你说,就是有,也是这个老头自己变异了,正常人毒瘾发作个一两次,命就没得了,这老头他妈的发作了十几年,还活蹦乱跳的,一万个吸毒的里头没有一个这么命长的,谁知道他是个怎么回事。反正看守所那边说了,不会有事,让我们放心。」
我一听这话,也有道理,而且就算他毒瘾犯了,也没啥别的辙,监狱里估计也有预备措施,轮不着我操心,就不再担忧这件事了。
不过之后的几个月里,我倒真看到了两次,这老头像是毒瘾发作的样子。但是别人毒瘾发作起来,跟疯了一样,自杀自残,跳楼点火,吞玻璃吃安眠药,干什么的都有,他却有意思,发作起来的时候,就往床上一躺,蜷成一团,手里拿着一包监狱里能买到的最廉价的那种咸菜干子,叫「下饭菜」的,浑身发抖,也不发出什么声音,就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,抖一阵子,往嘴里慢吞吞地塞一片咸菜,嚼吧嚼吧,也不见他咽下去,半晌才翻个身,脸上一抽一抽的,像是控制不住的肌肉痉挛。
我们怕他出事,就去问他怎么样,要不要去医院,他不吭气,就摇头,我们就让犯医在一旁守着,时刻观察他的情况,万一有什么突发现象。立刻往医院里送。可他也真能捱,看上去气若游丝的,就吊着最后一口命了,可这么抽着抽着,过个大半天的,自己也就好了,又能颤巍巍地下床,自己拿个瓷盆去领饭吃了。
渐渐地,我也确实发现了,火布古甲的身体,是真的靠着药硬撑的。
每天早上的时候,犯医和保健员都要推着小车,一个个监房去发药,每个犯人服药的种类都不一样,按照要求,必须当场吃下当场检查,绝对不准私藏。
别的犯人大多是高血压心脏病,或者一些特殊疾病,吃个两三种药了不得了,火布古甲每天要吃十一种药。早上七种,中午三种,晚上睡前还要特地吃一种。
我拉着犯医特地问过:「这老头哪来这么多药要吃?」
犯医也很无奈:「郑队,我跟您说句实话,这老头的内脏器官,简直就跟被狗啃过的一样,没一件是好的,各项指标,验血验尿出来的,也没有一项是正常的。你奇怪他怎么要吃这么多药,可我作为一名医生,我奇怪的是他都这样了,怎么还能活着的?」
「至于这么夸张?」
「比我讲的还夸张。这人体就跟一个电脑似的,你说这平时头疼脑热吧,顶多算是个软件问题,这个火布古甲就不一样了,他整个主机就跟三四十年前的老爷机一样,运行的还是dos系统,还全是病毒,你说,这种电脑现在还能开机,还能打字,是不是奇迹?」
他这个形容太过形象,我一下子有了画面感,但我还是奇怪:「照你这么说,这老头以前在外面这么穷,哪有钱每天买药吃?」
犯医叹了口气:「我跟您解释一下,这事是这样的。犯人进来,自己是不允许带药的,都是要进行入监体检之后,在医院根据检查出来的指标,和外面医院的诊断记录,来给病人配发药。这个火布古甲,在外头可能真不吃药,可在里面,按照监狱的规定,指标超标了、有什么毛病了,就得给他配什么药,这11种药已经算好的了,我怕吃多了他身体垮掉,跟医院那边合计了半天,捡情况严重而且药性不冲突的给他吃,最后缩减成了这11种。要不然的话,根据他那个体检报告啊,啧啧……」
说着,他看了看四周没人,冲我小心翼翼地伸出了五根手指,然后翻了翻:「……要吃的药的数量,起码得翻倍!」
「但他以前在外头不吃药,不也是活得好好的?」我还是觉得蹊跷。
犯医有些急了:「郑队长!我跟你说,天地良心,我给他开这么多药,对我半点好处都没有,我还嫌烦呢,你要是怀疑我,你只管查,看我有没有在中间搞什么猫腻!」
「不是怀疑你,就是就事论事,你跟我说清楚,我想不明白。」
「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?」犯医也没了办法,凑过来,把声音压低了跟我说,「以前在外面没人管,死了就死了,不吃药也没事,活过来算命大,可现在进来了,监狱能让他死在里头?你算算,是给他吃这些药花销大,还是死了之后人家属来闹事讹诈,索赔的数字大?您想想,就像去年七监区那个王——」
「好了。」我赶紧打断了他,「我听明白了,说到底,就是他福大命大,拖着个烂身子在外头硬熬着,不吃药也好,吸毒也好,被剁了手指头脚趾头也好,就是死不掉?」
「对头。可如今进监狱了,监狱总得管他不是?」犯医长出了一口气,「咱们里面这些措施啊,没问题。有问题的是他在外头的生活。别说您了,我比您更纳闷,他是咋还没死的?」
可说来也怪,就跟犯医老王说的一样,火布古甲在外头活得好好的,不吃药,不看病,甚至饭都不怎么吃得起,还吸了这么多年毒,仍然活的好好的。可近来这么又是挂水又是吃药的,养了半年,结果还是垮下来了。
他昏倒的那一天,是临近年关,腊月二十四,刚好小年夜的时候。
每年到了过年时,监狱就会统计「三无」犯人的数量,给予一定的补助物资,让每个犯人都能在里面好好过个年。火布古甲孤身一人生活,除了一个失联多年的女儿,没有任何别的亲人,账上也几乎没钱,自然也属于监狱重点补助的对象。
补助的物资不多,大概是百来块钱,加上一些糖果零食,还有一套新的贴身内衣袜子。文教交到火布古甲手上的时候,他还是没说话——这几个月来,他真的就像是听不懂汉话似的,每天一半时间躺在床上,另一半时间坐在位子上,就是痴痴地发呆,偶尔跟别人起纠纷的时候,他就从喉咙里发出嘶哑的吼声,以示恐吓,眼睛瞪大,身子半缩起来,绷得紧紧的。他从来未具有什么对别人的攻击性,却出于自卫,总是对周遭的一切表达出某种木木钝钝的敌意。
只是也少有其他犯人愿意与他起冲突,倒不是出于善念,而是单纯地害怕他身上真的沾染着什么溃烂的传染病,没有人愿意自找麻烦。
既然他在监狱里不惹事,不生事,文教也懒得跟他多说,就走个流程训了训话,便背着手走了。我站在门口看着,文教前脚刚走,后脚那刘瞎子就从床上晃晃悠悠起身,凑到了火布古甲边上:「怎么样,我给你算的,灵不灵?」
火布古甲从喉咙里咕噜了两声,伸出手,在送来的糖盒子里头捻了两块,扔给了刘瞎子。
我走进来:「刘瞎子,你给他算了啥,什么灵不灵?」
刘瞎子没想到文教人走了,我却还留在门口,脸上顿时挤出笑,把那糖往怀里一揣,「啪」地立正,敬了个礼:「郑队长——新年好!」
「少给我来这套,你们算了啥?」我没搭理他的做派,直接问道。
「没算啥,就是看他前几天喘的厉害,不忍心,给他起了一卦,算他这两天要交好运了,让他等着看。」
我嗤之以鼻:「统计发放三无犯过年物资,是监区每年这时候都有的。这也要你算?」
刘瞎子点头哈腰:「是,是。」
说着,他像是想起来什么一样,凑了半个身子过来,把我请到门边上,低声说:「不过郑队长,我跟您说句悄悄话,我那卦算了一半,还有一半,我没跟他说。」
从来只有犯人汇报思想,第一次见到有汇报算命结果的,大过年的,我也觉得有趣,就没打断他,让他继续说下去。
「他这一难,是遇水开河,遇山登梯,一波三折之相。前头有点小喜,可喜过之后,就是大灾,我估摸着就这么几天,得应在他身上,您可留个神,注意点。」
我转过头,打量了他两眼:「刘瞎子,你还有这么好心的时候?」
「什么好心啊,我是怕他死在咱们这监房里!我跟你说,我起了这一卦之后,就后悔了,谁知道能给他算出个死相来?我算出来了,因果就沾上了,要是他真死了,还死我眼前头,我还得在这监房里住几年,那是个完蛋,指不定『它』怎么缠上我呢……」
刘瞎子还在絮絮叨叨,我却把脸沉了下来:「胡说八道。你进来的时候,我怎么跟你谈话的?进来改造,就把你那套封建迷信的东西都给收起来!什么缠着你,有什么好缠的,你说!」
「是,是。」刘瞎子连连点头,「可这话啊,是个真的,您反正留个心,我也只能说到这了。」
说着,刘瞎子又拄着塑料拐杖,冲我敬了个礼,一瘸一拐地摸回床上坐着去了。
我当时不以为意,没太放在心上。可没想到的是,这瞎子一语成谶,没过两天,小年夜的那天中午,火布古甲就倒了。
犯医第一时间赶了过去,听了一下心压,再看了看他失禁的下半身,当时就说糟了,赶紧送去抢救。监内医院怕是不行,只能暂时急救缓解一下,赶紧联系外面的定点医院,要开车去送,要快,越快越好,不然人就没了。
监区立刻一边联系,一边向上汇报起来。由于关押犯人的特殊性,这种抢救的情况我们经历的不在少数,很快,狱内的急救车就开了过来,监内医院来的两名医生做了简单的心肺复苏之后,文教带着我和另一个内勤小杨,押着火布古甲就直奔外头的定点合作医院而去。
到了医院之后,早已经有医生和护工抬着担架在门口等着,直奔急救室而去。
我们在外头的椅子上坐着等,文教用对讲机和指挥中心正在沟通,做好了两手准备,无论救不救的回来,都要严格履行程序,并用警用监控设施记录下来全部过程,以免他那个失踪多年的女儿死后反而找上门来,跟我们「要个说法」。
幸运的是,没过多久,医生就出来了,告诉我们抢救很成功,也是运气好,我们送来的够及时,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。
按照以前的惯例,这种急病抢救的犯人往往还要在医院里住院观察一段时间,我甚至已经做好了今晚回不去,留在医院里通宵值夜班的准备了。可没想到医生摆了摆手,说不用住院了,直接带回去吧。
文教也有些意外:「不用再住两天看看?」
「有啥好住的,档案我看过了,这老头三十年吸毒史,现在这身体就是一摊子烂肉,能活着全靠命大,这已经不是医院能解决的问题了。」医生拍了拍手,「刚刚醒过来,有意识了,现在躺在那呢。你们谁签字?」
我跟小杨面面相觑,谁也说不出一个字来。
后来那个年,火布古甲还真的挺了过来。
不仅那一年,之后这几年里,他又陆陆续续地去抢救过几次,可说来也怪,每次都抢救得很成功,眼看着送去的时候印堂都乌了,只有进气儿没有出气儿的人,偏偏救完之后,回到监区里,又能活蹦乱跳地下床走路,自己吃饭洗澡了。
到了后来,连医院的急救室医生都认得他了,对这个彝族老头啧啧称奇,说救过这么多病人,这老头是身体最差,却是命最大的一个。
我们有时候议论起来,都说再这么下去,估计这老头连刑满都能熬到,还真有放出去的那天。
可是如果真到了放出去的时候,他又能干什么,又要怎么活呢?
没人知道。
不过,那也不是我们应该去想的问题了吧。